大学一毕业,我就到南京找男友云了。
云的表舅在南京有家公司,他毕业后一直在那儿工作,每个月拿1000出头的工资打发日子。我自己找了家小小的文化公司,每个月1000元的微薄收入,也算是高高兴兴上班了。
从此,我和云便开始了看似快活的生活。每天下班后便相拥着坐在租来的小屋里看电视,从下午六点的新闻到晚上十点多结束的黄金剧场再到深夜的午夜剧场。每天持续六七个小时,我们斜靠着廉价的充气塑胶沙发上,随着荧屏嬉笑哀乐,全身心地感受着荧屏上他人人生的丰富多彩。周末的时候就牵手去逛大卖场,拎回二三十元一件的衣服或其他便宜的物品,虽然关掉电视的瞬间我们也会突感空虚,眼见别人买房买车也会有一时的失落,遭遇权贵人士的冷眼也会一时激动感伤,可我们终究是似乎要满足于现状平庸度此生了。
日子无声地流逝了两年。
那天晚上,正当我们深深沉醉于电视剧离奇曲折的情节时,那台来自于跳蚤市场的17英寸老式彩电突然“嗤”地喘息一声,然后是一圈白光挣扎着晃了晃便寿终正寝了。我和云四目相觑,屋里难得的沉寂。我突然觉得虚飘飘空落落的,对面的老式三门柜镜中是两张麻木、呆滞的面孔。
我逃避似地捡起一本旧杂志翻了起来,那天晚上,我读了两篇小说,两篇散文;云则总结了我们两年来的存款—-168.6元。
第二天下班后,我读了卡夫卡的两个短篇和张爱玲的三篇散文,写了一篇500字的读书笔记;云看了两份报纸后跟我说: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存一个人的工资到银行吧。
第五天晚上,我写了一篇小小说投稿到晚报;云去图书馆听了一个关于市场营销的讲座。
第六天是周末,我们去了图书馆和书城,办了两张借书证,买了几本经济和文学方面的书。
第七天是周日,我在家看书、写稿;云则在精读《做一个成功的业务员》。
两个月后,我们的存折上有了3000元,我们没有去买电视机,而是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接下来,我报考了英语补习班;云找了一份做业务员的兼职工作。
我在报纸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云跑成了第一笔业务,拿到了1600元的提成。
一年后,我发表了文章100多篇,跳槽到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广告公司做了杂志编辑和策划,工资是原先的三倍;云又跑成了六笔业务。
两年后,我做了杂志的主编,有多家报刊约我写稿;云注册了一家广公司并开始良好运转。
今天上午,我们拿到了位于城中理想地带的新房钥匙;下午,我开始构思一个长篇,云计划年底把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万元升为500万元。
今天,恰好是我毕业第四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这四年,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两年。转变似乎是因为那台电视机的彻底罢工,可我明白,真正的质变是因为我们的醒悟。生活中有太多的暂时诱惑,也许是没完没了的电视节目,也许是刺激过瘾的电脑游戏,又或者是输赢无常的麻将……它们一点点侵蚀我们的时间,以看上去如此享受的方式,让我们沉迷其中乐不思蜀。它们让蓬勃朝气的生命一点点走向颓废,如同慢性毒药,渗透麻痹我们的思想。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力来抵抗,而强大免疫力的获得,来源于清醒的头脑描绘出的美好人生蓝图,并为之扎实而行,从而演绎起充实多彩的生活。
暗藏毒素的诱惑无处不在,请记得随时强化自己的免疫力。
—— 《青年文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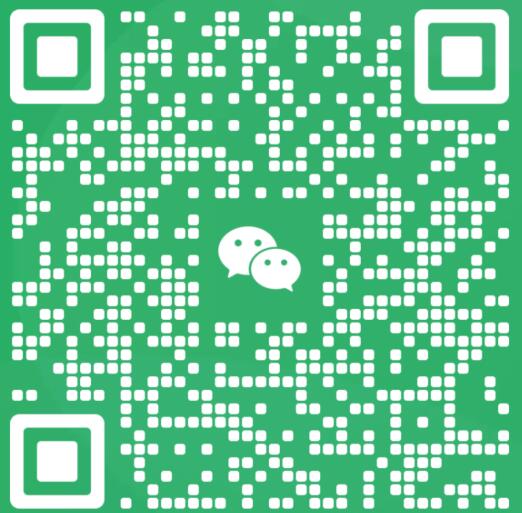

博主的主题很漂漂呀!